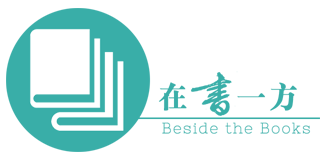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
《自由选择》引言
© 米尔顿·弗里德曼/文
Milton Fried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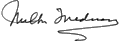
© 张琦/译


Milton Friedman
从欧洲的第一批移民定居新世界之后,美洲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这些移民来到美洲的目的各异,有的是来探险,有的是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迫害,有的纯粹是为了自己和子女们生活得更好。
移民潮开始时不过是涓涓细流,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移民速度逐渐加快,到19世纪终于汇集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千百万人横渡大西洋而来,另有少部分人横渡太平洋而来,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不堪忍受贫穷和专制带来的苦难,同时也是因为对美国的自由和富裕心向往之。
移民们来到美国时,并没有看到金砖铺地,也没有过上安逸的生活,但他们确实看到了自由和机遇,从而可以完全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着艰苦奋斗、精明强干、勤俭节约,外加一点运气,他们大多实现了自己先前的期望和梦想,给亲朋好友树立了榜样。
美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历史;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因为美国把两套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可能出于某种奇异的巧合,两套思想观念都在同一年面世,这一年便是1776年。
第一套思想观念体现在《国富论》这部伟大著作当中,正是这部书把苏格兰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推上了现代经济学鼻祖的地位。书中分析了市场机制如何能够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提供衣食住行等经济生产活动中所需的合作和协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关键的洞见是:只要协作是完全自愿的,那么交易双方就都能获益;除非交易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所有人都能通过协作获益,而这种协作并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力、强制,也不必侵犯个人自由。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观念体现在《独立宣言》当中,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这一宣言,表达了那一代人的普遍看法。《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人人有权追求其自身价值”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以一种更为极端和不容置疑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可以说,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围绕着《独立宣言》中的原则和理念而展开,是努力将这些原则和理念付诸实践的历史。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打了一场血腥的内战才解决这一问题)到追求机会平等,再到近来的追求结果平等,都反映了这种努力。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自由即可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而不必靠外部强制或某个中央命令,由此缩小了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域。而且由于自由市场是一种分散权力的机制,因此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能够被自由市场所克服、消化掉。如果经济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手中,那就必然导致专制、暴政。
19世纪,经济和政治自由结合在一起,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岁月。相比之下,美国甚至比英国更加繁荣,它的历史非常简单、清白:等级和阶级的历史残余较少;政府的束缚较少;土地更加肥沃,人们更有动力和活力去开发、去创造;并且还有一片广袤的大陆等待人们去征服。
自由的生命力,在农业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清二楚。《独立宣言》发表之时,美国只有不到300万人口,他们的祖先均来自欧洲和非洲(不考虑印第安土著),这些人都居住在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活动;要养活本国居民,并且要有一定的剩余农产品出口以换取外国商品,就需要9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今天,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不足5%,但却养活了2.2亿国民;并且,其剩余农产品之多,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奇迹的发生?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命令。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靠中央命令;在这些国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从1/4到1/2不等,然而它们到头来还是要从美国进口粮食,由此才能避免大规模饥荒的发生。就美国来说,在其农业生产迅速扩张的大部分岁月里,政府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美国确实开发了不少新的土地,但这些土地先前都是极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世纪下半叶,政府划拨出一些公地,成立了若干农学院;这些农学院靠着政府的资助,传播农业信息和农业技术,以此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但是,农业生产创新的主要源泉,仍然是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私人主观能动性,自由市场是面向所有人(除了奴隶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耻辱)开放的。奴隶制废除之后,农业生产得到了最快的增长。数百万人从世界各地移居至美国,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可以选择为自己工作,做一名独立的农场主或独立的商人;也可以选择为别人工作,只要双方都同意工作协议的内容。他们可以自由地尝试新技术,尝试失败就自担风险,尝试成功便可获利。他们很少受到政府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极少受到政府的干预。
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大萧条,在萧条期间和萧条之后,政府在农业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产量,由此把农产品价格人为地维持在较高水平。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正是由自由激发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新机械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发生;反过来,工业革命又有赖于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于是工业、农业便相互促进,齐头并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集权政府的权力视为对普通公民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保护公民免受专制政府的暴虐统治是必需的,而且永远都是必需的。这正是《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和《美利坚合众国权利法案》的宗旨所在;正是《合众国宪法》规定权力分散化的意图所在;也正是英国的法律结构自13世纪颁布《大宪章》以来至19世纪末不断发生变化的动力之所在。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而非运动员。杰斐逊心目中的政府,在其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1801年)表述得清清楚楚,他说:“政府应当是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防止人们之间互相伤害;但在其他方面,它应当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允许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事业。”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带来的成功,使它们对后来的思想家的吸引力日趋减少。到19世纪末,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它几乎没有什么集中的权力可以威胁到普通公民。但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使那些心地善良之人大显身手,做一番善举。然而这个世界并非完美无瑕,仍然有许多恶人恶事。实际上,社会愈加进步,恶人恶事就愈加显眼,愈加可憎。人们总认为社会进步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去仔细想一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进步。他们已经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会给自由带来威胁。相反,人们总惦记着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权力掌握在“好人和能人”手中,政府便可大有作为。
到了20世纪初,这些思想观念就开始对英国的政府政策产生影响。而且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接受这些思想观念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之前,它们对美国的政府政策并未产生多少影响。我们在本书第3章将会看到,美国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败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其实自建国以来,政府在货币领域就一直在行使权力。然而,不论是当初还是现在,人们都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大萧条的爆发应负有的责任。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大萧条的爆发正是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失败所导致的。这种谬论使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一道,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相对责任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此前,人们普遍强调个人责任,强调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现在却强调,个人不过是棋局中的一枚棋子,无足轻重,只能听凭外界力量的摆布。此前人们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其作用是防止个人之间彼此伤害、相互强制;而现在却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家长,既是家长,就有义务强迫一些人帮助另外一些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思想观念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发展方向。从地方到联邦,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在扩大,权力都在扩张;同时,权力和权限不断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政府逐渐承担起了收入再分配这一任务,打着保障、平等的旗号,从一部分人手中拿出钱来转发给另一部分人。为了“管理”我们“在工业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果”,政府接二连三地制定各种政策。这样做,其实是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过来了。
这样做本是出于好意,而且主要还是为了增进个人利益。但是,即便是最支持福利的父爱主义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实践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就像在市场上一样,在政府领域,似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其作用方向与亚当·斯密提出的那只手恰恰相反:一个人若想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促进公共利益,那么他便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来增进私人利益,而这却是“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一结论,将在本书各章中得到确凿而彻底的证明。我们将详细探讨政府运用其权力进行干预的各个领域,诸如追求社会保障(见第4章)追求平等(见第5章)、促进教育(见第6章)、保护消费者(见第7章)、保护工人(见第8章)、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见第9章)等。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到目前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迄今为止,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仍然是强有力的,其强大足以消除政治领域里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起到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带来的恶果。
近年来出现了增长放慢、生产率下降的现象,这自然引发了一个疑问,即如果我们继续授予政府更大的权力,同时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继续授权给公仆这一“新阶层”,把我们的钱财更多地交由他们支配的话,那么私人的创造力能否一如既往地消除政府管制带来的削弱作用呢?或者说,能否一如既往地克服其恶果呢?我们的答案是,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繁荣,迟早会毁掉《独立宣言》中以雄辩庄严的口吻宣告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
当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美国国民,我们仍然可以自由选择,究竟要不要在“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以此为其著作命名,该书见识深刻、影响深远——上减速慢行;或者,究竟要不要对政府权力施以更加严格的限制,从而更多地依靠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协作来实现我们的目标。长期以来,人类大多陷于集权专制的苦难深渊,即便是今天,饱受集权专制之苦的人仍不在少数,难道我们还要再次陷入这一深渊而结束我们的黄金岁月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远见和勇气来改弦更张,从经验当中学习,从“自由的重生”中获益呢?
如果我们想要做出明智的选择,那就必须对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则有一个透彻的理解。经济体制的原则即亚当·斯密提出的原则,它说明了一个高度复杂、高度组织化且运行平稳的经济体制,为何能够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发展繁荣起来;它说明了如何在不依靠强制的前提下实现人们之间的协作(见第1章)。政治体制的原则即托马斯·杰斐逊提出的原则(见第5章)。我们必须明白,用中央命令来代替自愿协作为何会带来种种弊端(见第2章)。我们还须明白,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值得庆幸的是,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欧各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政府的危害所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先前采取的种种政策表示不满。这一转变并不仅限于观念上,现实政治层面也开始有所转变。对议员们来说,持不同的论调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动,对其政治生涯越来越有利了。舆论导向也在发生重大转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促成其事,说服民众更多地依靠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彼此间的自愿协作,而不是依靠极端、彻底的集体主义。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探讨了在民主政体之下,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为何还会凌驾于人民普遍利益之上。此外还探讨了,为了矫正这种后果,我们应当如何弥补制度上的缺陷;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既对政府施以限制,同时又使其能够履行基本职能(即保卫国家不受外国敌对势力的侵略和破坏;保护每一位公民免受其他公民的强制;裁决国内各种争端;使大家能够一致认可应当遵循的准则等)。
本文选自《自由选择》,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D.弗里德曼/著,张琦/译,2013年6月第1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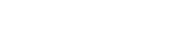
↓ 点击 阅读原文 查看英文书评

【编者按】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APAPA
Ohio及OCAA官方立场。所有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或来自网络。如存在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更多精彩文章,请查看我们公众号的主页。欢迎大家积极投稿!